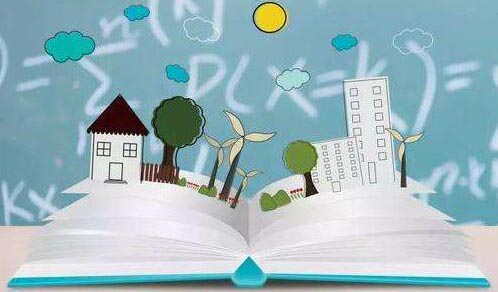2003年,我是幸福的,因為上帝讓我擁有了愛情,讓我擁有了你的智慧和聰明,讓我的肩可以讓你依靠,讓我的胸膛可以讓你遐想。
霞今晚不走了,我興奮不已,女友霞和我交往了半年多,從沒有在這里住過宿,今晚的破例,確實是我事先沒有想到的,霞很傳統,傳統的沒有讓我吻過她的額頭,今年27歲的霞曾有沒有過男友我沒問過。
心想半年來,我為霞付出了很多,今晚終于可以“美餐”一頓了,我坐著一切工作前的準備,買臉盆,毛巾,肥皂,牙刷,綠箭等等該買的東西都一一備齊了。
幾個月來,霞一直兩點一線地奔波著。我看在眼里,苦在心里。但霞從來不停我的勸說,她總是早出晚歸地從她那里出來,從我這里回去,有時是深夜凌晨2點,她也不會委屈自己,每當這時,我就扮演護花使者的角色騎車將她送到目的地,我再騎車回來,雖說亞運村到四道口,不是很遠,但來回還是需要個把鐘頭的。不知是怎得,我從來沒有拒絕過這種差事,說來也怪每次不僅不覺累,反倒覺得心情特別舒暢。
日復一日,從春走到夏,再到秋,香山的樹葉都紅了,可我的心里還是綠的。我還在為有這樣的生活津津樂道,為有霞的青睞而自我陶醉。
霞是中專生,文字功底頗為了得,寫一手好字,文章也寫的不錯,我雖披著主編“外衣”,若論真功夫,拿幾篇像樣的文章還真是急死人呢,可霞從來不因這個嫌棄我。
霞在我這里肩負著兩種工作,一是編校出稿,二是安慰我的心靈。盡管我知道烏托邦的意義,但這也夠難為她了,一個瘦弱的女子,能如此胸懷若谷,也可說是巾幗豪杰。
我出身農村,不善品食,又不善“包裝”自己,她總是默默地幫我改善生活,時常領我去一些有品味的“美食”店“渡渡”,有時也為我的衣著不整潔,沖我發些無名的火。我能理解,只是出身貧賤“陋習”,很難改,她為此給我一個綽號叫“土帽”,這也不怪她對我要求嚴,我的確從里到外、從吃到穿,從平時舉止到生活習慣,無不是現著“土”的光芒。
她面前,我這個“哥哥”像個小弟弟一樣聽話,有時也任性,而她這個比我小三歲的妹妹則像個姐姐那樣呵護著我,關愛著我,有時還在教育著我,也許你會嫉妒地說:“我不是男人。”“管得著么。”讓你羨慕去吧。
霞是我伯拉圖的第十二個色彩,霞又是我現實生活中的第一個“老師”。她教會了我很多,比如深入是生活,什么是愛情,什么是彼此關愛。
由于太激動,腦子里一下子浮現出了這么多的插曲,在到我辦公室的路上,這是僅有的對話。
后來,不清楚,是她俘虜了我,還是我俘虜了她,我們成了并肩作戰的同事,智慧里又包含著細致,使我們的合作天衣無縫,珠聯璧合。
“該休息了吧”霞把我從回憶中喚回,碟早已放完,時針已指向了3點45分。
“你睡那頭,我坐這頭。”霞一如姐姐的命令。
不睡呀?”我揉揉眼。
“我不想睡”,她用手理了理頭發。
“好吧,我們來個夜坐。”我半逗半調動情緒,我打破沉默的僵局。
“是嗎?”她臉露紅暈。
“怪我以前粗心沒有發現,風景這邊獨好。”
“去,貧嘴是吧。”她笑著要打我。
我沒有躲,她也沒有將手落下。
夜更深更靜了,窗外的星星像無數雙偷窺的眼睛,又像是一群好奇的孩子在偷聽我們的和風細雨。
夜更深更靜更暗了,我知道黎明快要來了,因為最黑的時候是黎明就要到來的時刻。
那一夜,我們沒有入睡——她在左我在右地坐了整整一夜,盡管是相視地坐了一夜,也算是滿足了我“一夜夫妻百日恩”的虛榮。
雖然,那一夜我們沒有故事,但那一夜是我們的“初夜”。而且是和一個自己心愛女人的“初夜”。我將永遠沉浸在那一夜的幸福里,永遠把那一夜珍藏在生命的記憶力。
如果有人問我“那一夜對你代表什么?”
我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他:“那一夜可以詮釋:“有多少愛可以重來”。